越来越多的家庭似乎都被困在了“关系”这个问题上。
许多父母觉得我都已经为儿女考虑这么多了,为什么他们“不肯”按照一般的社会规则(结婚,生娃)生活呢?
而许多年轻人又感觉哪怕物质条件不匮乏,但是和父母在一起就会很压抑,甚至于像结婚,生娃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在选项当中。
那这种代际的“认知”不匹配,抛开每个家庭的“个性化”问题不谈,有没有哪些“共性”的问题呢?
想回答这个问题,小伙伴可以思考一件事,保证我们在社会上生存的的最小单元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是一个答案并不统一的问题。
- 如果你问40后-60后,他们的答案可能偏向于第一个;
- 如果你问70后-90后,他们的答案可能偏向于第二个;
- 如果你问00后至以后,他们的答案可能偏向于第三个;
而之所以三代人有三个不同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变迁,背后折射的,正是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的一场深刻而无声的“原子化”进程。02
所谓“原子化”,简单说,就是传统的社会联结(如家族、邻里、单位)逐渐弱化,个人作为独立的“原子”,直接面对国家、市场和社会洪流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经济越发展,技术越进步,我们反而越活成了一个个“孤岛”呢?圆方觉得,答案要从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去寻找,也就是我们初中政治课本所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对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极弱。一个人单打独斗,很可能一场天灾或一场大病就陷入绝境。
于是,人们必须“抱团取暖”。这个“团”,就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家族。
家族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微社会”:它组织生产(种地)、提供保障(族田、祠堂救济)、负责教育(私塾)、甚至执行司法(家法)。
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完全镶嵌在家族的脉络里。所以,对于我们的祖辈和父辈(40后-60后)而言,“家族”是他们生存安全感最根本的来源。而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情况变了。
工业化需要什么?
需要自由的、可流动的劳动力。工厂和公司需要的是一个个能随时上岗、能根据生产需要四处迁移的“标准件”工人,而不是一个拖家带口、根系复杂的家族成员。(包括当年的农业合作社和一系列“运动”,本身也是对于过往大家族体系的重塑)而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加速强力地解构传统的家族纽带。它用“公司”取代了“家族”的生产功能,用“社会保障体系”(医保、社保)试图替代家族的保障功能,用“公立学校”承接了家族的教育功能。这时,社会生存的最小单元,就很自然地缩小了。一对夫妻带上孩子,组成一个核心家庭,就能很好地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
- 这个单元足够灵活,可以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跨市甚至跨省迁徙;
- 它的消费欲望也更强烈,构成了驱动经济增长的内需基础。
- 70后到90后这一代人,正是在这个转型期中成长起来的。
他们大多脱离了庞大的家族网络,但又普遍生活在由父母构筑的家庭港湾里,因此,“家庭”是刻入他们骨髓的认知。那么,为什么到了00后及以后,连“家庭”这个单元都似乎变得不那么牢靠,极度的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了呢?答案藏在技术的爆炸性进步和制度的深度变迁中。
首先是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个体获取信息、知识、娱乐和社交满足的成本急剧降低。
过去,许多情感支持和娱乐活动需要在家庭内部或邻里之间完成;现在,一个智能手机就能搞定。饿了有外卖,闷了有短视频和游戏,烦了可以找网友倾诉。技术提供了一套极其高效的“个人生存解决方案”,使得个体对传统共同体的依赖度大大下降。
同时,像“计划生育”这样的国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客观上加速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让许多年轻人自出生起就是家庭的中心,更习惯于独立决策和自我负责。更重要的是,现代服务业和金融的发达,为“单身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租房、买保险、享受各种上门服务,而不必非得依靠婚姻或家庭来分摊生活成本和风险。03
今天的中国,其实依然是三代人的不同认知共存的。
40-60后是“家族共同体”的尾声见证者,70-90后是“核心家庭”的典型体验者,而00后则是“个体崛起”时代的原生居民。
而这种不同的认知,其实也是当今许多深层家庭矛盾和代际矛盾的底层原因。并非谁对谁错,而是他们分别站在了历史演进的不同坐标点上。某种意义上来看,原子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和选择权,但同时也伴随着孤独、焦虑和意义感的缺失。 而当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社会的凝聚力、信任成本、乃至生育率等根本问题都会面临挑战。未来的社会,或许需要探索一种新的“协作体系”。不是在形式上回归大家族,而是在尊重个体独立的前提下,基于共同的兴趣、价值观和数字技术,构建起新型的、自愿的、温暖的“微共同体”。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需要共同书写的答案。
社区如何向外部输出价值观
前面几篇写了公司和社区的不同维度的对比分析,本篇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视角,秩序输出的角度来看待不同的组织形态,无论什么样的组织形态,都嵌入到更大的系统中,对外输出秩序,如果耗散的速度大于负熵产生的速度,组织就走向瓦解,反之组织程度会加强,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种理解组织的方式。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组织协作
公司向外输出秩序,是一个基于经济共同体的强协作组织,它可以稳定地对外输出秩序。评价一个公司好或者不好,产品的角度来进行或者从服务的角度来进行。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当这里些东西和外部环境发生联系的时候,它会对外部环境的进行重塑。如果我们把这个组织过程看做一个黑盒子的话。那么对它的输入输出来进行评价,就是它所消耗的资源和它所产生的外部价值。
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价值是一个很难交换的东西。互联网第一波只是交换信息,但到了第二波希望能够交换价值,因为价值的核心就是要大家有一个共识。在一个Distributive System(分布式)系统里面,达到共识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每个网络的节点都有时间的延迟,计算能力也不一样。有的计算机有良好的行为,有的计算机确实有一些不良行为。在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里面,如何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这在那个计算机科学里面也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计算机科学中有一个Fischer-Lynch-Paterson 定理,在采取一种完全Deterministic(固定)算法的时候,共识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因为这个网络的系统实在太复杂。
后来,大家就想到区块链的技术可以把经济行为加上随机的数学算法使得网络达到共识,比如说通过计算一个Hash函数的办法,对共识进行投票,这就是整个区块链上面达到了一个新共识的机制。
大家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共识的机制本身会有很大的价值。事实上物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熵增,就是物理世界看起来是总是走向无序。但是生命世界和物理世界不太一样,生命世界确实越来越走向有序。走向有序的行为是把熵减少的一个行为,但是整个系统的熵还是在增大。因此,生命行为就是把自己的熵减小了,使周围的熵增大了。
这在共识机制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达到共识就是要把熵减少,大家如果意见非常不一样的话,熵也就很大,因为非常无序。但是如果能够统一意见,达到一种非常有序的状态,它必然是减小熵的一种行为。然而,减少熵的行为必然会增高周围世界的熵。
因此,当时提出来的算法是通过一些 Hash函数的计算,这虽然看起来是浪费了一些周围世界的能量,其实得到了一种更可贵的财富,也就是共识。
在这个意义下,区块链的共识系统有点像生命系统本身,自己的熵在减弱,它达到了共识,但使得周围的系统熵变大。这是一个代价,但相比别的系统来讲,这个代价还是非常小。
《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世界新的分合转折点》张首晟
分布式组织形式如何稳定向外输出秩序?
作为社区形态的组织也需要向外输出秩序,这些高度冗余的人力资源体系,如何构造为一个强协作,可以实现确定性交付的组织呢?在公司里面是通过职位进行固定分工,灵活性相对不足。而纯粹的社区又因为太灵活,缺少一部分相对固定性的职能分配。
这里面塑造这些分工的背后的机理,从公司组织里,其实是财务流在进行支撑,每个分工有自己的最大收益函数。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也就是说通过财务这种激励的引导等和和和其他的这种引导如何让参与分工的人达到自己收益函数的最大化,而这个个人收益函数的最大化,又能够和组织收益函数的最大化相匹配,达到一个平衡。
图片
公司是单核的,社区可不可以是多核的?
如果把组织看做一个电脑的话,那么公司对外展现为一个强处理器,这个处理器是在内部进行一系列的分工。而社区相当于是说有多和结构多个功能主体,每个都是一个小蜜蜂,然后这些小蜜蜂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超个体的生态组织。
图片
公司是套娃结构,社区可不可以是蜂巢结构?
几乎所有的公司都面临一个套娃困境,CEO是这个公司外面最大的那个套玩里面是这些套玩要想挣脱外面这个套娃的束缚,是一个天然的瓶颈。而对于蜂巢组织结构,当蜂王死了之后会有新的蜂王产生。整个蜂王在组织过程中其实产生的也不是一个CPU的角色。
当一个蜂群被分散之后,这个蜂群又会产生新的一套独立的组织体系。就好比这个干细胞分化为特定功能的细胞,特定功能的细胞很难再分化为干细胞。而社区组织蜂巢组织则具备这样反向分化的功能,就好比蚯蚓截断一阵儿之后还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图片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社区对外可以做一个小的整体。对于社区所属的一个大的组织结构,又可以作为一个部分。其实在大公司里面也是这样子,一个小的事业部对外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对那又是一个小的部分,只是这个小的部分没有自己的一个财务核算权力,这个可以对应为数学上分形结构。
未来的组织,不是单纯的公司属性,也不会是单纯的社区属性,而是一种融合的属性,形成复合的嵌套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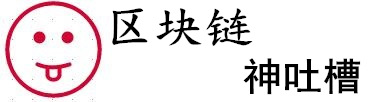 区块链神吐槽
区块链神吐槽